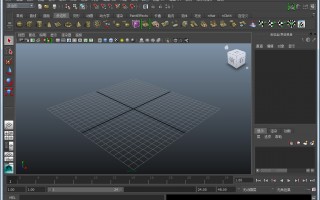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总承包公司《创新丰富文化载体 助推企业跨越发展》
公司简介:
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于1995年4月8日成立,是中建三局成立最早的支柱型直营公司,综合实力连续十余年位居中国建筑所属工程局直营公司前列,被誉为“中国建筑直营公司的优秀排头兵”。
目前,公司合同额超600亿元、营业收入超200亿元,经营区域覆盖湖北、河南、山东、天津、湖南、广东、海南等10余个省市及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高端房建、基础设施、机电安装、高级装饰、投资开发、海外等全产业链经营格局。公司先后整合了8个局内单位,孵化分立了局北京公司、混凝土公司、房地产公司、成都公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公司等优质公司,为企业转型发展作出卓越贡献。
成立24年来,承建或参建了雄安市民服务中心(千年雄安第一标)、天津117大厦(571米)、武汉站(全球最美建筑)、武汉中心(438米)、武汉天河机场T2T3航站楼、河南省郑州市科技馆新馆等大批重大工程。获鲁班奖(国优奖)32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项、国家专利146项、省部级以上工法160余项,多项工程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全国市政金杯奖、全国用户满意工程、全国建筑业新技术应用金牌示范工程奖。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用户满意企业、中央企业先进集体等荣誉。
企业文化理念体系:
激情成就事业,文化引领发展。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负着为局集团“增强实力,培养人才,积累经验,提高信誉”的历史使命,始终坚持高起点运作,高标准要求,在《中建信条》、《十典九章》和中建三局争先文化的引领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融入其中,历经“创业孕育‘三品’——开拓形成‘三品’——跨越彰显‘三品’”三个阶段中,逐步形成了“三品”企业文化理念体系。
企业核心理念:杰出品牌、卓越品质、高尚品位。杰出品牌体现在品牌经营上,即承接品牌工程,建设品牌项目,创造品牌价值;卓越品质体现在品质管理上,即注重品质塑造,控制品质过程,实现品质发展;高尚品位体现在品位员工上,即提升品位形象,培育品位格调,倡导品位生活。
企业使命: 拓展幸福空间。
企业核心价值观:品质保障、价值创造。
企业品格: 敢为天下先,永远争第一。
企业愿景: 争当中建集团高品质发展的领先者,中国建筑业卓越营造的领先者。
企业精神: 诚信、创新、超越、共赢。
企业发展观:坚持“三高战略”(主攻高端市场、高端客户、高端项目);“差异化”战略,包括塑强细分领域品牌、扩大海外业务增量、抢占水利水务先机、提升投资运营效益四个方面;“两高一低”战略:高品质、高效率和低成本,即在高品质的前提下压降无效成本,高效率地提供客户所期待的产品和服务。
人才观: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高能、有为”的干部队伍。
在“三品”总包文化理念的影响下,形成“两个核心优势、三个核心能力”。
两个核心优势是指: 出众的文化优势。“三品”文化理念凝聚着企业拼搏奋进、处处争先的创业豪情,感召着员工对大格局、高品位的追求,它是企业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是实现跨越发展的灵魂支撑。强大的人才优势。公司先后向外输送副处级以上干部120余名。人才资源是公司最宝贵的财富,也是谋划未来的最大底气。
三个核心能力是指: 一是开拓能力。公司坚持内外兼修,始终葆有“公投”和战略客户“两把市场营销利剑”,以“亮剑”的精神直面市场搏击,24年来在国内开拓13个区域。二是融合能力。先后整合8个局内单位,吸纳接收上千名员工,让许多单位扭亏为盈,成为公司重要支撑;在选人用人上,坚持“五湖四海、海纳百川,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的方针,以宽阔的胸怀、良好的机制把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企业发展中来。三是再生能力。坚定不移走改革创新之路,并按照“授权有度、集中有序、监督有力、分级负责”的管理授权体系,优化企业治理体系,提升运营管理效能。
创新丰富文化载体 助推企业跨越发展
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在中建信条·争先文化的引领下,通过丰富文化内涵、彰显文化魅力、拓展文化空间,发挥文化引领优势。作为基层单位,企业文化的落地深植才是关键,在做好规定工作的同时,总承包公司更致力于结合企业实际和员工需求,在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致力于持续创新和丰富文化活动的载体,真正把企业文化的“软实力”转化为企业发展的“硬支撑”。
一、注重载体的争先引领,丰富文化内涵
1.文化铸就杰出品牌。公司将企业文化建设融入到企业发展战略之中,注重价值观的引导,使品牌形象在经营生产中得到有力彰显。一是文化引领,瞄准发展高目标。总承包公司在创业发展的过程中,确定了高瞻远瞩的品牌文化,始终把“高起点运作,高标准要求,快节奏运行,建一项工程,树一座丰碑”作为经营战略,七年时间即跨入局集团第一方阵,身体力行践行争先品格,引导企业和员工去实现一个又一个更高的目标。在初期创业文化的引领下,迅速凝聚了员工共识,激励员工不断追求卓越,攀登高峰。二是文化砥砺,创造发展高速度。公司敢于突破常规,瞄准高端,争分夺秒去“抢”、千方百计去“拼”、有胆有识去“争”,诠释争先文化内涵。在实现高位增长的同时,公司将文化理念逐步拓展延伸,经过不断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提出了“杰出品牌、卓越品质、高尚品位”的“三品”理念,并迅速融入到中建信条·争先文化当中,推动企业从“做强建造主业”到“投资+建造”两轮驱动转型发展的华丽嬗变,引领公司连续十余年位列“中国建筑工程局直营公司排头兵”。三是文化导航,占领发展高平台。公司抢占建筑市场制高点,敢于争先,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把品牌积累转化为用品牌搏击市场的实力,以战略眼光和超前思维谋篇布局,加快企业转型,在新时代提出了“争当中建集团高品质发展的领先者,中国建筑业卓越营造的领先者”的战略目标,实现企业跨域发展,这些都与中建信条的核心理念高度匹配和适应。
2.文化创造卓越品质。公司注重将文化理念融入到各项管理环节,坚持抓文化就是抓发展,在管理上遵循“决策科学化、运营程序化、手段现代化”,积极把企业文化建设与制定完善的管理体系和管理制度集合起来。在全局乃至中建系统率先以“法人管项目”理念建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率先在中建系统内构建具有领先水平的“全能型”和“全候型”项目管理模式,争当总承包管理模式的实践者、新业务模式的先行者和法人管项目的首创者;在推进“两化”融合的过程中,不断修缮和改进企业发展的制度、规章和流程,率先在全局启动管理梳理和诊断提升,自主投入和研发中建系统第一个项目业务管理综合信息系统,获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大幅提高基础业务的工作效率;在企业风险防范与管理中,率先在全局建立项目风险分级管理和过程预警机制,建立起“授权有度、集中有序、监督有力、分级负责”的管理授权体系。有效的管理文化成为支撑企业战略发展和有效提升执行力的重要手段,使企业文化的触角融入到企业管理的“血液”里。
3.文化成就高尚品位。公司坚持“企业进步与员工发展并重”,将中建信条、争先精神和十典九章深植在项目上,展现在行为间。为让员工深入理解《十典九章》与自身岗位和发展的联系,公司设立“业务知识考试、第三方综合素质考核、民主测评评议”的“1+X”的竞聘模式,搭建人员能进能出、薪酬能增能减、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通过定期组织文明礼仪培训,定制符合CI形象的工作服,开展同岗位技能比武、每周文明办公评比等,坚持用企业文化塑形象,用企业形象规范员工行为的理念。通过每月公示文公流转效率情况,每周通报“夜间巡查”情况,以作风建设推进企业文化建设,考评服务作风。通过开展“新员工下班组”活动,建立“业务导师、思想导师”双导师制,让高校毕业的青年员工初尝“泥土味”,在基层中淬炼,在互帮互助中成长。
二、注重载体的与时俱进,彰显文化魅力
1.用文化的凝聚力实现共鸣。公司青年员工操石杰,连续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白血病女孩的生命。在他的事迹感召下,公司成立了三局首支以员工个人名字命名的志愿服务队——“操石杰”青年志愿服务队,其小善传大爱的举动逐步汇聚起一支800余人的志愿服务团队,随后成立了农民工志愿服务小分队和“蓝宝”志愿服务队,精准构建“1+1”志愿服务体系和“五色行动计划”,用具体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新风。公司先后荣获湖北省“荆楚学雷锋示范团队”、“荆楚学雷锋示范点”“湖北省第四届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多人获评“中国好人”“天津好人”“湖北好人”、湖北省“向上向善好青年”。另一位“草根明星”火会燎,则是从农民工到公司中层骨干的全国优秀进城务工青年的典型代表。湖北省总工会首次为农民工火会燎“立传”,组织编写的励志书籍《农民工火会燎》,被列为全国工会示范职工书屋必配书籍。公司成立了湖北省首个以农民工姓名命名的创新工作室“火会燎创新工作室”,他个人也获评“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除此之外,还有“多年捐资助学”的周文君、“垫钱救人”的李旺、“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叶建、“湖北省十佳农民工”徐彬、“工地小候鸟的守护者”张华、走上大学讲堂的农民工杜晓波、潘云德等一大批总包工匠,这些接地气的典型事迹,既达到了学习标杆的作用,更是文化的一种落地。
2.用文化的渗透力实现共赢。公司积极与劳务合作伙伴、材料供应商、战略客户等签订《企业文化共建协议》,开办项目暑期“工地幼儿园”,坚持构建党建工作“大联盟”的格局,持续开展三号联创、三联建等活动,将中建信条·争先文化向合作伙伴延伸拓展,增强文化的感染力。公司还与各级检察院开展“检企共建”活动,共同建立信息交流与情况通报、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廉政档案、效果评估五项制度,通过组织参观检察机关办案区和警示教育基地、开展预防讲座及法律咨询、合作拍摄廉洁微电影、自编自演廉洁情景剧等活动,让“诚信、公平、超越、共赢”的企业精神所倡导的现代商业伦理成为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推动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此外,公司宣传文化工作始终将“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贯穿始终。编印188期《品总包》杂志,并根据职工的需求不断改版创新,“人物”、“现场”“文化”等讲述身边故事的栏目深受职工喜爱。员工创作的《品位总包》人物风采录、《《激情总包》、《魅力总包》、《青春总包》、《幸福总包》、《诗意总包》《原创音乐集》等系列文化产品,记录员工的成长、担当和幸福。编印《年度企业形势任务口袋书,推出《华夏之巅》《筑梦雄安》系列文集等,全程记录企业跨域发展和国家战略工程、重点工程的建设实录,为企业发展留下宝贵经验。
3.用文化的影响力实现共享。担当社会责任是企业软实力的重要表现。近年来,公司全方位关爱农民工,率先在全国推行劳务实名制管理,实现劳务工人全职业周期管理,在局内首次创新开展工会联合会样板评选活动,持续开展“模拟法庭进工地”、农民工集中入会活动,全面维护工友权益。打造了“农民工婚纱照”“农民工集体婚礼”“工地亲子照”、“农民工子女夏令营”等活动品牌,获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上百家主流媒体的持续报道。与《湖北日报》合作策划了《酷暑,农民工的另类生活》专题报道,一个月内连续刊登10篇共计2万字的新闻报道,彰显了中国建筑的社会责任。此外,公司还先后向贫困学校和困难学子捐款100多万元,向第八届全国艺术节、第六届全国京剧艺术节等提供赞助。在抗震救灾、冰雪抢险、道路清障等任务中,勇于担当政治使命和社会责任,彰显央企风范。公司先后获得“中央企业抗雨雪冰冻灾害先进集体”、全国“抗震救灾、重建家园”工人先锋号等荣誉。
三、注重载体的创新驱动,拓展文化空间
1.创新老办法。一是创新活动形式。公司连续举办五届企业文企业文化节,通过企业文化实践活动、员工才艺展示及技能竞赛发布企业文化成果等,引导广大员工加深对企业文化的理解。公司每年斥资百万打造“温暖、健康、幸福”三大工程,先后20次组织500多对青年通过集体婚礼形式走进婚姻殿堂,根员工职工个性化需求成立摄影、篮球、健身、主持近10个协会,满足新时代下员工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围绕中国结构第一高楼天津117大厦、“千年雄安第一标”雄安市民服务中心、滁州惠科电子厂房等重大项目建设,设立党员突击队、青年安全文明示范岗,广泛开展“进项目、进班组、进岗位、进系统”的四位一体“工地英雄”系列“工地英雄”劳动竞赛,掀起施工生产高潮。多年来,公司持续组织春节健步走、十二届游泳比赛、十一届足球赛、七届篮球赛、六届乒乓球比赛、五届职工运动会、四届羽毛球赛、红歌赛等一系列群众性文化活动。《工人日报曾》这样评价:“中建三局三大工程实践属于员工的‘中国梦’”。二是创新服务载体。通过举办“微电影”活动,使员工被重视和关注。其中,微电影《民主管理那些事》获得“湖北省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微电影大赛”一等奖,《无悔青春》网络点击突破100万,《回家》获10万+网络观看,在网上掀起一阵热议建筑人生的风潮。三是创新党建载体。公司实行“党员积分制”动态管党员,量化考核党员综合表现,以党员的示范引领带动广大员工精神面貌的提升;首推党建“标准化课程、标准化阵地、标准化培训、标准化系统”,解决建筑企业点多面广,培训难集中、阵地难统一、党费难收缴、工作难考核等难题;首创“微党课、微论坛、微分享”一体化的“三微”季度党建品牌活动,以小切口聚焦大视野,一季一主题,讲身边事、身边人、身边理,改“一人讲”为“大家讲”,变“单一枯燥”为“生动活泼”,提升党员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创意和灵感。
2.拓展新办法。一是构建文化建设新阵地。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公司充分发挥新媒体优势,通过在办公平台设置“党务公开”、保密在线、“两学一做”等专栏,使企业管理理念得到认可;通过开设“品总包”“清廉总包”微信公众平台、总包青年微博、“品总包”抖音等,每日将企业大事、好事及最新政策及时推送传播,促使企业文化落到实处。二是拓展文化建设新思维。公司掀起“互联网+”大讨论活动,青年员工围绕“互联网+企业文化”发表看法,公司领导班子建立了 “互联网+”微信讨论群,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对建筑业的未来发展、企业的战略转型、精细化管理、人才队伍培养、文化建设等进行了火热讨论,使企业不断适应当今的新常态和信息万变的新时代。
3.用好硬办法。一是领导带头,落实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在每年新员工培训班上讲授文化建设专题,基层党政“一肩挑”领导每年必讲一次文化课。各级领导人员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带头践行,有效发挥了文化示范引领作用。二是过程考核,上下联动。将文化建设纳入各基层党组织的年度目标责任状,建立企业文化建设与生产经营、人才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等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开展、同考核的管理机制,并开发党群考核系统,根据“差异化+动态”的考评体系,按照“创优+达标”两类目标,实现文化建设线上考核、工作日清日结。三是反馈评估,双管齐下。建立政工干部同城业务竞赛制度,把中建信条的宣贯学习作为竞赛内容,竞赛结果与政工干部薪酬和晋升挂钩。建立工作预警机制,在对基层支部的季度考核中要求推动文化建设必须有方案策划、实施记录、经验总结,落实不到位、排名后2位的,会上领黄牌,发言作改进,确保文化建设“精准定位”、“掷地有声”、“抓铁有痕”。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永远在路上。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将继续以《中建信条》、《十典九章》为精神旗帜,不断强化文化体系的执行力,提升文化管理的渗透力,增强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坚持“三品”总包核心理念,为实现“两个领先”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小善”聚大爱
从2016年6月底开始,吉林省洮南市科技馆副馆长庄严多了个职务——洮南市“日行一善”公益众筹助学项目账户管理员。每天下班后,庄严都要抽出大量时间接收爱心捐款、回复爱心人士的微信留言,还要统计和发布捐款账目。就是这样一份既没有薪酬也没有休息日的“兼职”,给了庄严无限的收获与快乐。
2016年1月10日,由洮南市委宣传部打造的“日行一善”全民助力脱贫攻坚活动拉开序幕,倡导全社会成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每人每天做一件好事,帮助贫困群众解决日常生活困难。
帮助困难群众实现微心愿是“日行一善”最初设置的活动主题之一,收集整理好的微心愿借助“公益洮南”微信公众平台发布,让爱心奉献有的放矢。在这个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很多微心愿都是关于急需生活必需品的问题。于是,2016年5月28日,洮南市“日行一善爱心捐赠站”成立。在这里,志愿者们接收捐赠物品,并将物品清洗、消毒、整理、贴标签,摆放整齐。贫困户可以来领取物品,也可以选择通过志愿者或者洮南市邮政局的爱心邮包送达。
洮南市委宣传部文明办主任金玲说:“捐赠站成立当天就收到了物品7000多件,捐款3万多元。随着捐赠物品和领取人数的不断增多,洮南市又发动一些城区沿街店铺设立‘爱心物资代收点’,组织有条件的村成立爱心捐赠分站,为困难群众建起了家门口的免费自选超市。”
聚沙成塔,小城洮南被志愿服务的热情所笼罩。2016年6月8日,“日行一善”又发起了助学捐款活动,采取每人每天捐一元钱的公益众筹方式,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金玲介绍,为了方便沟通并确保捐款公开透明,洮南为爱心人士建立了“益路同行”微信群,并招募志愿者负责统计和发布捐款账目。捐款的爱心人士中有96岁的老党员,有省下零花钱的学生,有收入不高的普通职工,甚至还有拾荒老人。截至2018年年末,“日行一善”公益众筹助学项目累计募集资金400余万元,资助城乡贫困家庭学生达1500多人次。
目前,微信群已达到7个,账户管理员志愿者有9人。庄严说:“我们9个管理员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忙,却依然乐在其中,因为这里时时刻刻都有感动。”
为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洮南市还创新设计了“志愿服务+”项目,鼓励每个人根据各自能力、特长、职业优势等参与到扶贫项目中。2016年4月22日,洮南市聚宝乡黑顶村组建了第一支农民志愿服务队,驻村第一书记闫海义担任队长,领着驻村工作队队员、村里的年轻干部和返乡就业青年为乡亲们服务。
如今,洮南市221个行政村全部建立起农民志愿服务队,有2000余名农民志愿者,提供留守老人儿童亲情陪护、村屯卫生保洁和治安巡逻等志愿服务。(记者 任爽)
相关问答
澳门一肖一码必中一肖今晚MBA平板兼容APPv6.9.5_图吧地图
带他们看看科技馆让他们眼界更加开阔我希望我可以为农民工子弟的生活贡献一...成都市慈善总会小善慈善基金理事长曾在报社、电视台等媒体担任记者、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