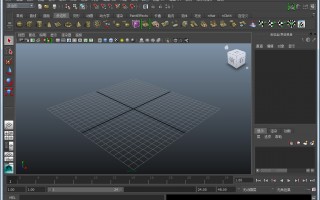蛇咬、虫蜇……如何应对常见动物伤害?
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
蛇咬、虫蜇……如何应对常见动物伤害?

我国常见的10种毒蛇。受访者供图
6月3日,游客李先生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家人在海南三亚旅游期间被蛇咬伤,经两家医院接力救治后,于6月2日清晨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对此,三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目前,调查组联合省级专家组正加紧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等待更多信息披露的同时,很多网友表达了对蛇咬伤为代表的动物伤害的担忧,不知该如何处理。
常见动物伤害包括蛇咬伤、昆虫蜇伤和宠物咬伤,如何认识与应对?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赵斌。“对不同的动物伤害有不同的处置方法,专业性很强。”他说,“动物伤害的第一时间都在院外,医务人员不在现场是大概率事件,这就需要非医学专业的人员学一些专业的动物伤害的救治技术开展自救。”
每年10万—30万人被毒蛇咬伤
每年5至8月是蛇类活动高峰期。被蛇咬了怎么应对?
“蛇咬伤是常见的动物致伤疾病。”赵斌说,无毒蛇咬伤主要造成局部损伤,毒蛇咬伤则会造成一种急性全身中毒性疾病,这是毒液从伤口进入人体内而引起的。
赵斌表示,由于毒蛇咬伤发病急骤,病情发展迅速,若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救治,蛇毒可迅速在体内扩散而影响机体多器官功能,导致机体代谢紊乱、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粗略估计,我国每年的蛇咬伤病例达数百万,毒蛇咬伤为10万—30万人,70%以上是青壮年,病死率约为5%,蛇咬伤致残而影响劳动生产者高达25%—30%,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
已知世界上现有蛇类2700多种,其中有毒蛇600余种,而对人有致命危险的主要毒蛇有195种。在我国各省份都有蛇的分布,但大部分蛇种集中于长江以南以及西南各省份。我国常见的十种毒蛇分别为:五步蛇、蝰蛇、蝮蛇、眼镜蛇、银环蛇、烙铁头蛇、竹叶青、眼镜王蛇、金环蛇、青环海蛇。
被毒蛇咬了是怎么发病的?
关于毒蛇的发病机制,赵斌表示,有四种,分别为:血液毒、神经毒、细胞毒、混合毒。
血液毒指的是,蛇毒蛋白酶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血管壁,破坏血管壁的有关结构,诱导缓激肽、组胺、5-羟色胺等的释放,直接损害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抑制血小板聚集,而导致出血。蛇毒溶血因子可直接作用于血细胞膜,使其渗透性和脆性增加。
“神经毒素主要为α-神经毒素(α-neurotoxin,α-NT)和β-神经毒素(β-neurotoxin,β–NT),分别作用于运动终板(突触后)的乙酰胆碱受体和运动神经末梢(突触前)。α-NT竞争胆碱受体,β-NT抑制乙酰胆碱释放,再抑制其合成,均可阻断神经—肌肉传导,从而引起神经肌肉弛缓性麻痹。”赵斌说,“最常见的此类毒蛇有银环蛇、海蛇、金环蛇。”
至于细胞毒,赵斌介绍,蛇毒中的透明质酸酶可使伤口局部组织透明质酸解聚、细胞间质溶解和组织通透性增大,除产生局部肿胀、疼痛等症状外,还促使蛇毒毒素更易于经淋巴管和毛细血管吸收进入血液循环,进而出现全身中毒症状。
此外,蛇毒中的蛋白水解酶可损害血管和组织,同时释放组胺、5-羟色胺、肾上腺素等多种血管活性物质;心脏毒素(或称为膜毒素、肌肉毒素、眼镜蛇胺等)则会引起细胞破坏、组织坏死,轻者局部肿胀、皮肤软组织坏死,严重者出现大片坏死,可深达肌肉筋膜和骨膜,导致患肢残废,还可直接引起心肌损害,甚至心肌细胞变性坏死。
混合毒就是上述三种毒的叠加。
4种蛇毒的临床表现各不相同
关于蛇咬伤的常见症状,分无毒蛇和有毒蛇两种。
“无毒蛇咬伤部位可见两排小锯齿状的牙痕,伴有轻微的疼痛和(或)出血,数分钟出血可自行停止,疼痛渐渐消失,局部无明显肿胀、坏死。”赵斌说,“全身症状不明显,可表现为轻度头晕、恶心、心悸、乏力等,部分患者会出现全身过敏表现。”
而有毒蛇咬伤依据其蛇毒种类不同,其临床表现也各不相同。赵斌介绍,按蛇毒的毒素类型,其临床表现可分为四类。
血液毒。此类蛇毒成分复杂,包含出血毒素、凝血毒素以及抗凝血毒素,具有多方面的毒性作用,主要累及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以及泌尿系统。局部表现为咬伤创口出血不止,肢体肿胀,皮下出血、瘀斑,并可出现血疱、水疱,伤口剧痛难忍。全身表现为各部位出血,如鼻腔、牙龈、尿道、消化道,甚至颅内可出现出血;血管内溶血时有黄疸、酱油样尿,严重者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合并DIC(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时除全身出血外,还会出现皮肤潮冷、口渴、脉速、血压下降等休克表现。
神经毒表现为咬伤创口发麻,疼痛不明显,无明显渗出,常常被忽视。早期症状轻微,1—4小时后可出现头晕、恶心、呕吐、流涎、视物模糊、眼睑下垂、语言不清、肢体软瘫、张口与吞咽困难,引起呼吸肌麻痹,最终可导致急性呼吸衰竭甚至自主呼吸停止。
细胞毒可导致肢体肿胀、溃烂、坏死,可继发心肌损害、横纹肌溶解、急性肾损伤,甚至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混合毒可表现两种及两种以上毒素引起的症状,如眼镜王蛇咬伤以神经毒素表现为主,合并细胞毒素表现;五步蛇咬伤以血液毒素和细胞毒素表现为主。
只要被蛇咬伤,都应按毒蛇咬伤处理
“没有经验的人很难立即分辨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咬伤。因此,只要被蛇咬伤,都应按毒蛇咬伤处理。尽快呼叫救护车。让患者休息,不要活动,以免加速毒液吸收。”赵斌说。
赵斌表示,绑扎的目的仅在于阻断毒液经静脉和淋巴回流入心,而不妨碍动脉血的供应,与止血的目的不同,故绑扎无需过紧,松紧度掌握在能够使被绑扎的肢体下部(即远端)动脉搏动稍微减弱为宜。
赵斌提醒,不要切开或挤压伤口,也不要吸吮伤口。最好记录蛇的颜色、花纹、长度、头部形状等,或在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将蛇打死送到医院,帮助医生诊断。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动物也有喜怒哀乐的情感。一般动物在大自然的生存中,出于保护自身的原则,会遵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赵斌说,动物可以成为人类的朋友。
处置昆虫蜇伤,先看伤口有无毒刺
常见的昆虫蜇伤主要有蜂蜇伤、蝎蜇伤。
据赵斌介绍,蜂蜇伤是因蜂尾部毒针刺入人体皮肤,并将毒腺中的毒液注入而引起的局部或全身反应,它是一种生物性损伤。我国常见的蜇人蜂有蜜蜂、黄蜂、马蜂。蜜蜂刺入人体后将毒刺留于刺伤处;其他蜂类大多将毒刺缩回,可继续刺入,偶尔也留下毒刺。
关于蜂蜇伤的常见症状,赵斌表示,局部有剧烈刺疼、灼热红肿,严重出现水疱或淤血,皮肤变色,甚至坏死。还可能引起过敏反应,严重时出现喉头水肿、支气管痉挛等。黄蜂蜇伤还可以发生溶血。
蝎蜇伤是因蝎子尾部末节有一根弯形呈钩状的毒刺与毒腺相连通,人若被蝎刺伤,其毒液注入人体,对人的局部和全身均有一定的毒性作用。全世界蝎子有几百种,我国主要有全蝎和东北蝎。它们滋生于热带和亚热带。
“蝎子蜇伤以手足多见。蜇伤处皮肤红肿,中间可见蜇伤斑点,内有钩形毒刺,严重时引起局部水疱,甚至坏死,同时可伴有蜇伤处疼痛、麻木、感觉异常。”赵斌说,“轻者没有全身症状,重者蜇伤1—2小时后,会出现头昏、头疼、流涎、流泪、视物模糊,甚至发生抽搐、休克和昏迷。”
对于昆虫蜇伤的现场救护方法,赵斌介绍,首先检查有无毒刺或毒囊残留在皮肤内,发现毒刺要尽快取出,最好用针挑出,不要用镊子夹出,以防夹刺时将毒囊内毒液挤入体内。
用肥皂水充分清洗患者伤处。其次,冷敷患者伤口,以延缓毒液吸收,减轻肿胀和疼痛。最后,尽快送到医院救治或呼叫救护车。
清洗伤口,阻止和减少毒素的吸收是救治的核心
随着养宠物的人群越来越庞大,人们既享受到了与宠物和谐相处的快乐,也可能遭遇意外的宠物咬伤。
赵斌表示,家养宠物狗、猫的唾液中常带有狂犬病毒和细菌,人被狗、猫咬破皮肤后有被狂犬病毒感染的可能。而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人兽共患病,致死率达100%。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每年全球狂犬病病例约5.5万人,其中80%发生在亚洲,大约50%是15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
据赵斌介绍,狂犬病患者的伤口会出现疼痛、红肿。如果感染狂犬病毒,患者数天至数个月后可能出现烦躁、惶恐不安、牙关紧闭、怕光怕水等狂犬病症状,严重时危及生命。
“一旦被宠物咬伤,应立即用清水和肥皂彻底冲洗伤口,把伤口内的血液和动物的唾液清洗干净,冲洗时间不能少于20分钟。如果伤口很大,软组织损伤严重,则不可冲洗过度,防止引发大出血。”赵斌说,若是开放伤口,不要包扎,并尽快把患者送到医院治疗,及时注射狂犬病疫苗及破伤风抗毒素。
最后,赵斌提醒,清洗伤口,阻止和减少毒素的吸收是救治的核心。而救治的最低期望值,是不要给伤者带来二次伤害,包括对伤者的身体和心理。边救治,边联系有能力接收伤者下一步治疗的医院,不要盲目送医。(记者 熊建)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科学家与企业家如何同题共答?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题: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科学家与企业家如何同题共答?
新华社记者温竞华
一个顶刊好成果,为啥出了实验室却进入不了市场?科学家有成果,企业有需求,为啥总是匹配不上?
近日,记者旁听了一场特别的闭门研讨会。会上,数十位来自科研一线的青年科学家与数十位上市公司负责人围坐一桌,直面科技成果转化的痛点难点,坦诚交流、各抒己见,在碰撞中寻求“解题思路”。
《2024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53.3%。相比之下,2022年的调查显示,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9%。
“我既是科研人员,也在学校里负责成果转化工作。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是当前我们在科研产业化上面临的一大痛点。”作为最先发言的人之一,华东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院长杨强开门见山。
杨强的一番话说到了在场科技界专家和产业界代表的心坎里,引起大家争相发言:
“科学家思维与企业需求存在天然鸿沟,科学家更关注技术的先进性,但企业还要关注产品的性价比、有没有市场,双方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科研人员攥着成果但不知道怎么和投资人对接,需要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
近年来,从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到拓宽科技创新的融资渠道;从试点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到加快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的新路径。
记者在研讨会现场看到,科技界、产业界和社会力量正在努力探索、改变,推动科学家和企业家同题共答、双向奔赴、各得其所——
深圳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江旭晖分享了自己转变思维的心路历程:“过去我们是‘带着锤子找钉子’,堆了很厉害的技术却产生不了好的应用效果;现在我们学着‘遇到钉子打造合适的锤子’,让市场和企业的应用需求倒逼我们研发和优化,半年解决了3个合成数据产业化难题。”
“科研方向与市场需求就像两条平行线,而企业可以凭借对行业的深入了解,精准找到二者的结合点,把两条线拉到一起。”中重科技董事长马冰冰说,企业在发展中一直与高校保持密切合作,有效促进高校研究成果与企业产品结合落地,机器人等智能化技术在冶金行业有着广阔应用前景,是企业未来希望对接的方向。
作为中国科协主管的全国性公益基金会,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近期联合近200家上市公司和1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国家级创新中心,共同发起成立了“青年科学家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旨在推动成果转化向“需求牵引型”转变,通过产业沙龙、孵化营、项目对接等模式,帮助青年科学家和企业家精准匹配,探索产学研对接长效机制。
南京大学副教授程文、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教授冷雨泉和山东新华锦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联合体的受益者。近日,在基金会和联合体的搭桥下,两个科研团队和企业围绕电子皮肤、外骨骼机器人等达成合作协议。
“通过基金会和联合体的‘需求池’匹配,我们在康养产业上的技术需求和两个团队的研究成果一拍即合,从技术对接到与科研团队成立合资公司,跑出了产学研合作新速度。”新华锦国际董事长张航说。
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宋军介绍,联合体后续将按细分领域组织精准对接,首批聚焦机器人、生物制造、AI应用三个赛道,“我们希望搭建起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深度融合的平台,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
研讨会由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主办,主题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路径”。
相关问答
富士康哪个部门最好呀?搞技术的就哪些部门呀?哪个地方的厂最有前途呀?哪位知道,在下感激不尽?
技术部门好些(制工、产工、研发),生产第一现场已经没有前几年的发展好了,毕竟现在扩张没有那么快了,管理岗位基本上饱和!目前富士康在全国深圳、成都、昆山...
为什么有的人总觉得高学历就应该拿高工资?这是什么心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低学历就没有什么竞争优势了,可能以后工厂里的工人,学历都要大学本科文凭。而你小学毕业的,根本没办法跟他们交流。现在中国也在升级产业...
2022年什么行业发展前景好?
一名优秀的美容师,在日本在韩国都是很有前景!美容业成本低,利润高。只要有办法(比如:办会员,这属于捆绑式消费。)留住客源,把口碑做出来就好。我国目前的行业...
cnc调机员新手多久能学会?
CNC调机员新手的话,大概半年可以学会。因为新手气学调机的话,它有一个流程要走,就是你首先要学会机床的面板和程序的结构,然后工艺的安排和道具的安装和使...
目前国内哪个投资理财平台靠谱?请有经验的给推荐一下?
朋友们好,非常明确回复投资人:目前的确有一些正规可信,产品有特色,经受住历史考验,口碑好的投资理财平台。今天就和朋友们来分享。分享的第1十实,投资理财...即...
在殡仪馆工作,具体都有哪些岗位?哪个岗位的待遇最好?
别问我为啥知道的这么详细,读到最后你就知道了![捂脸]在殡仪馆工作,具体都有哪些岗位呢?第一个岗位:遗体化妆师遗体化妆师干啥活?顾名思义,就是活人给...醒醒...
想去部队当女兵,去部队之前想学点武艺,学什么好呢?
想当女兵,就将身体锻炼好就行了,所谓的学点武艺?是要准备到部队当侦察兵还是特种兵?1.可以肯定的说,学武艺可以,但是到了部队不一定有你表现的机会,毕竟...现在...
委比正数和负数是什么意思?正数好还是负数好?_作业帮
[回答]委比是衡量一段时间内场内买、卖盘强弱的技术指标.它的计算公式为:委比=(委买手数-委卖手数)/(委买手数+委卖手数)×100%.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委比...
写好字的重要性作文不少于300字_作业帮
[回答]汉字有着鲜明的文化性、艺术性、技术性、独特性.所以,我认为仍需要把字写规范、端正、美观.而电脑打字只是手写汉字的辅助手段,它不可以也不能代替...
电子科大的电子系研究生就业情况怎样?哪个专业相对好些?
电子科大研究生就业不存在问题,更何况是电子专业的,就电子科学与技术下的二级学科来说,电磁场与微波技术是我校的王牌专业,就业非常好,本科生都很好,何况研...